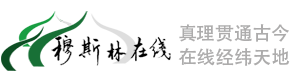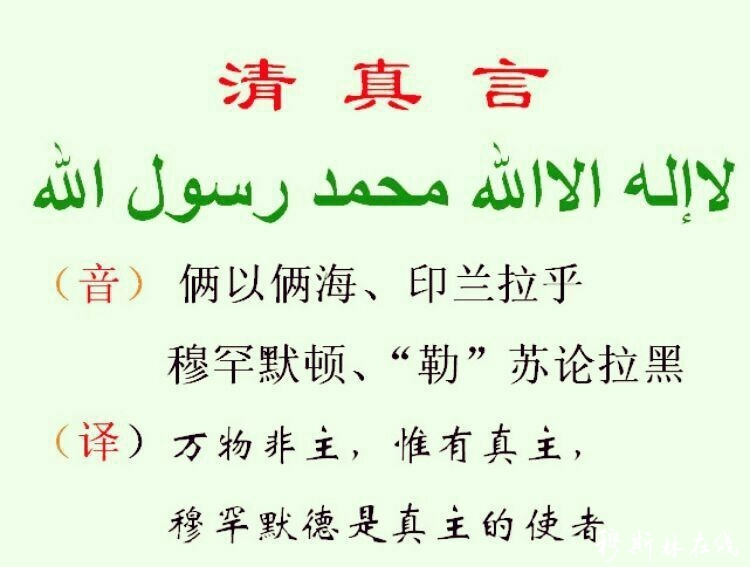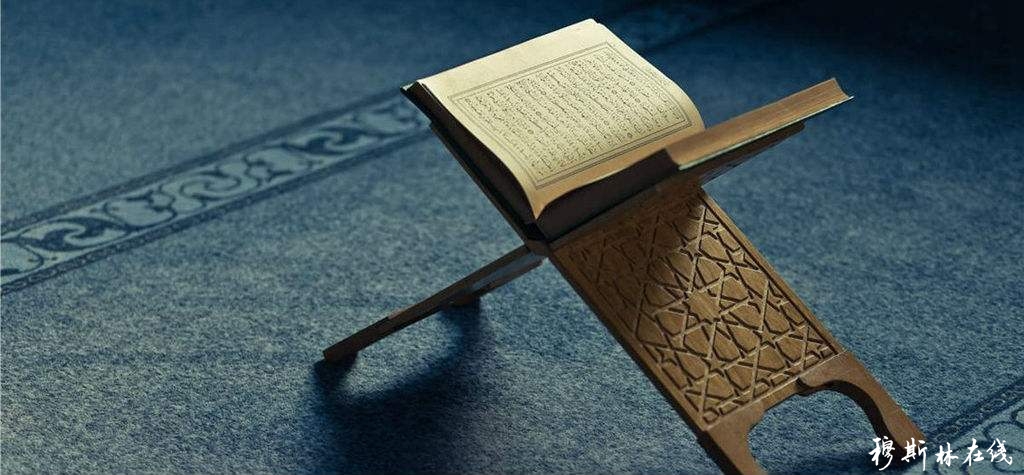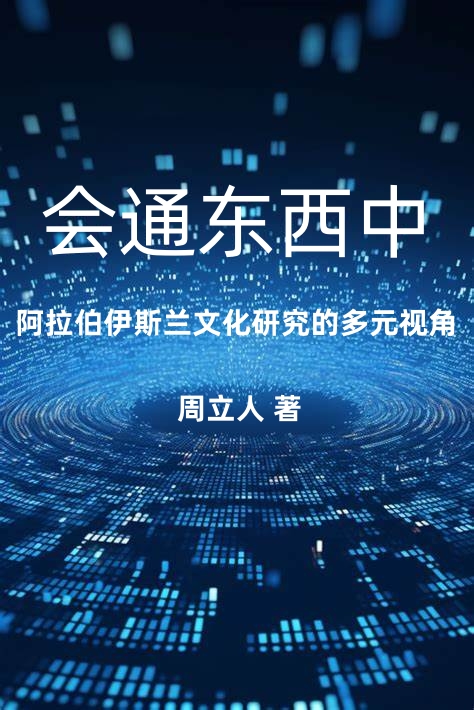三、人性美
伊斯兰美学的第三个核心内容是人性美。根据伊斯兰教义,安拉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又创造了人类,并让人类担任他在大地上的代理者。《古兰经》上说:“当时,你们的主曾对众天神说:‘我必定要用泥土创造一个人,当我把他创造出来,并将我的精神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你们当为他而倒身叩头。’”(38:71-72)“当时,你们的主对众天神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2:30)这个代理人便是人类的始祖阿丹。安拉不仅赋予人以优美的形象——“他曾创造了你,然后,使你健全,然后,使你匀称。”(82:7)“他以形象赋予你们,而使你们的形象优美。”(40:64)——,而且更重要的是赋予人以思辨能力:“他以智慧赋予他所意欲的人;谁禀赋智慧,谁确已获得许多福利。惟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2:269)也就是说,人因为有了思辨能力便能最终将自己跟一般的动物区分开来,便能自觉地运用它去发现隐藏在宇宙万物背后的自然定律,并且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逐步摆脱蒙昧主义,让自己焕发出人性美的活力和光芒。
伊斯兰人性美的内涵包括“认主独一”、行善、坚忍、施舍、宽容、求知和奋斗等基本内容。伊斯兰认为:“认主独一”是人性美的首要前提,拜物、拜金、拜偶像、拜多神的人,其人性必然扭曲甚至异化,必然给人的社会带来诸多的危害;行善能在抵御各种邪恶、克服人自身种种弱点的同时不断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水准,为建构公正、公平与和谐的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坚忍能磨砺人的意志,使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勇敢而又乐观地应对各种挑战;施舍能戒除人的贪欲,洗净自己的灵魂;宽容能化解仇恨和矛盾,进而建立起和睦友善的人际关系;求知能启迪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让人们不断地参悟到宇宙的奥秘并更好地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奋斗能让人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让人们以奋然向上的姿态去面对人生,为建立伟岸高贵的人性之塔添砖加瓦,从而实现自己崇高、远大的理想。
关于“认主独一”,《古兰经》说:“信士,只是确信真主和使者。”(49:15)关于行善,《古兰经》说:“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势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势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16:97)关于坚忍、施舍和宽容,《古兰经》说:“他们是为求得主的喜悦而坚忍的,是谨守拜功的,是秘密地和公开地分舍我所赐给他们的财物的,是以德报怨的,这等人得吃后世的善果——常住的乐园,他们将进入乐园。”(13:22-23) 关于求知,《古兰经》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35:28)穆罕默德说:“谁走上了求知的道路,安拉必使他踏上直达乐园的坦途。”[1]关于奋斗,《古兰经》说:“你们当尽力而工作。”(6:135)“能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人,这等人,确实是诚实的。”(49:15)
另外,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教诲,伊斯兰所弘扬的人性美还包括:诚实践约、自律节制、团结协助、谦虚戒骄、尊老爱幼、民主协商、耿直公正、清洁卫生、以礼待人等等。
伊斯兰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善向上的,人性美是安拉赋予的。《古兰经》说:“你们应当趋向正教,并谨守安拉所赋予人的本性。真主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30:30)而基督教神学的“原罪”说则认为,人与生俱来的是罪性,罪性是人的本性,它是邪恶和苦难的根源。人无法摆脱原罪,因此才有基督甘负十字架牺牲自己来为人类承担苦难的悲壮“圣迹”。当然,基督教也崇尚善良、公正、同情和友爱等美德,这些美德对于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佛教则把人性定义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即瑜伽行派所说的“根本心”,常意译为藏识、宅识等。小乘部派佛教只建立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而瑜伽行派却认为在此六识的深处,还有一个不断活动且导致生死轮回的根本心,它就是阿赖耶识。最先提出阿赖耶识的是《解深密经》。从佛教的教义来看,佛教各宗派对阿赖耶识有着不同的解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阿赖耶识是由如来藏与无明和合而生的,属于真妄二性和合之识。换句话说,人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善,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恶,而是两者的混合。[2]然而,佛教又把人性看作是一种虚无的东西。佛教认为,人由五蕴,即色(物质、肉体)、受(喜怒哀乐)、想(理念活动)、行(意志活动)、识(统一前几种活动的意识)组成,但五蕴是无常虚幻的,最终要分离消散,归于寂灭,因而人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本体实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性的本质是无,是空。那么,人性的本质既然是无,是空,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佛教把生命的意义寄托在佛性上。 禅宗甚至认为佛性即是人性,佛从自身求,不须向外觅,只要直指本心,便能顿悟成佛。禅宗很赞赏大乘佛教《维摩经·佛国品》中的一段话:“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也就是说,只要内心觉悟,人人都可以达到佛性的崇高境界,所居之所亦即成为净土。由此而知,佛教虽然否定经验世界的美,但却崇尚超验世界的美(如“佛性”之美、“净土”之美)。在这种以寂灭(无相无知,无欲无念)为特征的至乐至美的精神境界里,人的一切烦恼和痛苦都荡然无存,一切愚痴和执著都化为乌有。这真可谓一种超越人生和世俗的大美大乐。关于净土(即极乐世界)的由来,《佛说无量经》载:“世自在王如来住世时,有国王因闻佛法,发无上正道意,弃国捐王,出家修道,号曰法藏。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佛前发下了48条度生大愿,普度有情。”其中有:“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最后,法藏比丘请世自在王佛为其广说210亿诸佛国土的情状,并且以此作为蓝本,经五劫之后,以大愿力创造了这个极乐世界;法藏比丘成佛后号阿弥陀佛,也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教主。关于“净土”之美,《万善同归集》所引《安国抄》载有“24种乐”,所引《群疑论》载有“30种益”,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彼岸的、超验的美。佛教认为,人生的最高旨趣在于证得佛性,进而达到涅槃。涅槃具有“常乐我净”四德。常者,涅槃之体,恒不变而无生灭;乐者 ,涅槃之用,缘灭而永安永乐;我者,涅槃之主,性不易而真实;净者,涅槃之性,不为幻尘所污染。《无量寿经》中说:“佛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佛以究竟证故,常享常乐我净之法乐。众生以彻底迷故,恒受生死轮回之妄苦。”如果说,基督教认为苦难是铸造高尚灵魂的场所,那么佛教则认定转迷成悟、离苦得乐的“涅槃”是人性美的最高境界。当然,这时的人性已不再是真妄二性和合的阿赖耶识,而是人性在剔除了妄性之后所剩下的真性。
儒家则主张以“仁”为核心的人性美。孔子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意谓和讲仁义道德的人相处,这才是美。而且,孔子一方面以“仁学”作为儒家美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当作实现仁学,完善人性的必由之路。然而,孔子人性审美观受其恢复和维护周礼的最终目的的制约,有着明显的保守色彩。儒家的这一保守性在《周易》中也时见一斑:“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周易·坤》)意谓摆正自己的位置,坚守礼制的体统,美德便在其中了,而身体力行,在事业中发扬,那就堪称完美无缺了。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人性美的思想,即把人性和审美相联系。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意谓口对于滋味,有相同的嗜好;耳对于声音,有相同的听觉;眼对于容色,有相同的美感。谈到人的内心,唯独就没有相同之处了吗?人的内心的相同点又该是何物呢?那就是理和义。圣人只是早先得知了这一点。所以理和义对于我们内心的愉悦作用,就好比家畜的肉能让我们大饱口福一样。孟子的比喻似乎有点低俗,但却很直观、很坦率、很平易地表达了理和义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美的感受。在他看来,人性美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养心”来培育一种“浩然之气”。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一旦养成了“浩然之气”便可达到超凡入圣的美好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这显然将人性美过于神化。当然,孟子有关人性美的论述也有针对现实的,如他认为廉洁是人性美的一种表现:“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意谓哪有君子可以用钱财来收买的呢?这句话对于我们当下的反腐倡廉仍然具有启迪与警示的作用。
对儒家美学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易传》,则通过解释筮文来描述“美”,并且采用了与阴阳相关的隐喻和象征手法来突显出人性之美。如:“亁,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但由于认识论上的神秘主义特点,不少比附很难令人信服。这一点在董仲舒有关人性的论述中也能找到,如他也喜欢将人与天相作比附,说:“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道家喜欢从自然或超然的角度来审视人性之美,如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把“仙真”之美当作人性之美,认为仙真之人傲世出尘,与世无争,致虚守静,物我两忘,无己无待,并且能以永年之术龟鹤遐龄。他还认为:有真人而后才有真知。“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庄子·大宗师》)意思是:真人不预测先兆,不妄自尊大,也不谋虑未来;他们有过错的时候不后悔,有功劳的时候不得意;这样,他们即便登上高处也不会感到恐惧,落入水中也不会被水濡湿,进入烈火也不会感到灼热。只有当认识上升到与大道合一时才有可能达到如此的境界。由此可见,道家倡导的是超功利、超世俗的人性美,其结果往往很容易将人们引向追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道路(道教的产生便是一个例子)。
对于庄子的人性美,袁伯诚在《庄子的诗意人生追求与诗化哲学》中作出这样的评价:“庄子与老子不同之处是,庄子反文化的理论立场把哲学诗化而导向美学,他试图通过追求一种超声色之美的审美心理,使人类的审美精神得以净化与提升,达到彻底超功利超社会的状态。人类的心灵净化了,提升到澹然无极的境界,美的事物就自然集于一身,就能‘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庄子创造的丧失自我与‘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带有十分浓厚的神秘色彩。”[3]袁伯诚在这里所说的“丧失自我与‘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如果用18世纪德国诗人席勒的话来说,就是“外在自然”(客观的世界)与“内在自然”(人的本性)的融为一体;即在自然被人的纯朴情感与理念人格化的同时,人格也在同自然的和谐中被自然化。
通过探讨伊斯兰美学以及其他宗教或哲人的美学思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伊斯兰所倡导的和谐美、中正美、人性美是建立在“认主独一”信仰上的审美观。它是宗教和现世、宗教和美学相结合的典范。三种美相辅相成、交相生辉,构成了互动关联的欢愉向上的美学共相。伊斯兰美学在研究的对象上,在审美的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与其他美学所不同的特色。
其他美学除了以上论及的内容外,还有不少是属于各种文艺流派的一家之说,也就是把美学定义为“研究人的艺术活动,包括创作与欣赏的特征和规律的科学” [4]。比如西方的古典主义美学、表现主义美学、直觉主义美学、形式主义美学、客观主义美学、心理距离说美学、自然主义美学、实用主义美学、精神分析学美学、符号论美学、分析主义美学、新托马斯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美学等。它们虽然标新立异、各执一端,但却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其中大都是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副产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常仅仅以艺术作为探讨美学问题的出发点,并且将对审美诸问题的研究限定在经验和假说的范围内。古典主义美学主要注重美的形式,如毕达哥拉斯把圆形和球形视为美的最理想的形式,柏拉图把美的形式的创造看成是来自上帝所赋予的灵感,他还指出,作为整体意义上的美的结构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5]亚里士多德把美的要素归结为“秩序”、“匀称”和“明确”,他在《诗学》中指出,戏剧作品的情节具有统一性的特点,所有的部分都是紧密相连的,以至于最后能满足人们对“秩序”、“匀称”诸要素的期盼。阿奎那也强调美的“完整性”和“鲜明性”。此外,他们大多认为,一切作为美而存在的形式都统一于审美主体的心理感受,而这种心理感受的普遍特点就是“感官的满足”和“精神方面的享受”。柏拉图说:“真正的快感来自所谓美的颜色、美的形式,它们之中有一大部分来自气味和声音。总之,它们来自这样一类事物:在缺乏这类事物时,我们并不感到缺乏,也不感到什么痛苦,但是它们的出现却使感官感到满足,引起快感,并不和痛感夹杂在一起。”[6]亚里士多德说:“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为不仅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幸福正是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结合。”[7]
而中国传统美学也往往只把艺术形式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如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里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甚至轻视美的作用和意义:“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有些古代典籍只是将世上没有害处的一切事物笼统地界定为“美”:“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国语·楚语上》)或者把有残缺的、不纯的东西当作美:“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还有的认为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此为美兮,在彼为蚩。”(刘禹锡《何卜赋》)
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强调美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性。他说:“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8]康德在完整系统地阐述美学基本原理时,认为美学既不是哲学的简单延伸或附带部分,也不是同文艺理论相混淆的诗论。他从审美经验和“逻辑设定”两个层面来构建他的美学思想。谢林认为,美学不同于哲学的地方在于美学把整个人(而不是人的一小部分)引向认识的最高点,在有限的感性形式之中表现出无限的意蕴。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他说:“美是理念,即概念和体现概念的实在二者的直接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须直接在感性的实在的显现中存在着,才是美的理论。”[9]在他看来,“感性的实在”就是艺术化精神生活中真与善所依赖的物质性。博克的美学思想可以说是集中代表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博克在承认美的客观性的同时,探讨崇高感和美感的生理及心理基础。他认为,崇高感主要是建立在恐惧和痛苦等心理倾向之上的,因而与以延续种族为目的的涉及“自体保存”的情欲相关,而美感是人选择性欲对象所考虑的因素,所以与以“爱”为内容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情欲相关;二者均只涉及客观事物感性方面的即用感官和想象力来掌握的内容,因而理智和意志在这里都不起作用。弗洛伊德认为:“美没有明显的用处,也不要刻意的修养。但文明不能没有它。美学科学考察了事物的美的条件,但是它不能对美的本质和起源作任何说明,像往常一样,失败在于层出不穷的、响亮的、却是空洞的语词。”[10]他认为“对美的爱,好像是被抑制的冲动的最完美的例证。‘美’和‘魅力’是性对象的最原始的特征。”[11]尼采则说:“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12]他把人作为美的崇拜对象:“如果试图离开人对人的愉悦去思考美,就会立刻失去根据和立足点。‘自在之美’纯粹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一个概念。在美之中,人把自己树立为完美的尺度;在精选的场合,他在美之中崇拜自己。”[13]
当然,在西方美学史上也有人(如席勒、谢林等)曾强调审美活动的意义在于培养具有自己行动意志的自由的道德人,在于改造人类社会,在于洞见绝对同一的本原世界。然而,如果缺少对绝对、永恒的价值实体的真实信念,缺少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对于宇宙中无限高明的精神,所怀有的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心情”[14],似乎很难将有限的产生于经验世界或感性世界的美填进无限中去。
[1] 引自安萨里《圣学复苏精义》上册,张维真译,商务印书馆2001版第10页。
[2] 受此启发,宋明理学把人性看做由“天命之性”(善)和“气质之性”(恶)相杂而成。而明末清初的回儒学派又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性”与“禀性”之说,认为人性“有二品:一真性,二禀性”(《清真指南》)。
[3] 袁伯诚:《庄子的诗意人生追求与诗化哲学》,《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4] 德国哲学家鲍姆加敦1735年在《诗的哲学默想录》中首次提出“美学”(Aesthetica)的概念,并把它界定为“研究感性完善”的一门新学科,有时又称之为“研究感官判别的科学”和“艺术的哲学”。他的美学著作主要讨论诗歌和戏剧。
[5]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6]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页。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8]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9] 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9页。
[10] 弗洛伊德:《论升华》,参阅《弗洛伊德谈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11] 弗洛伊德:《论升华》,参阅《弗洛伊德谈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12] 尼采:《偶像的黄昏》,参阅《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22页。
[13] 尼采:《偶像的黄昏》,参阅《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21-322页。
[14] 《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