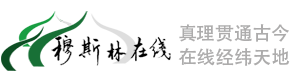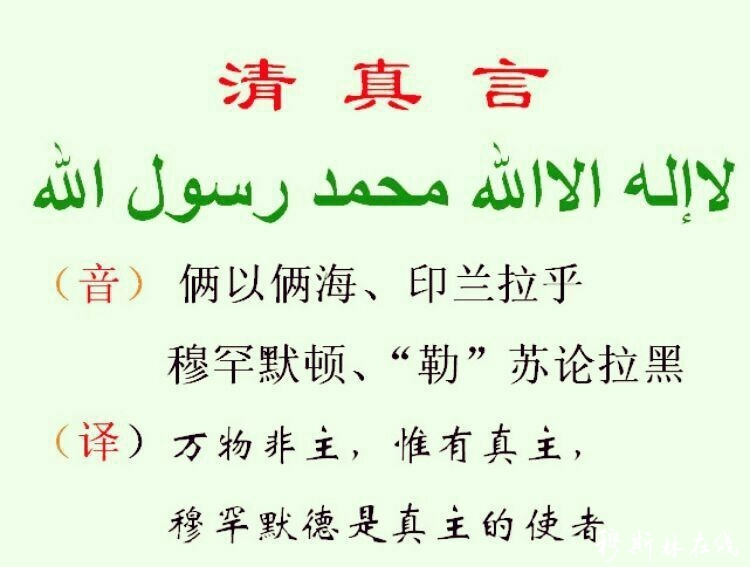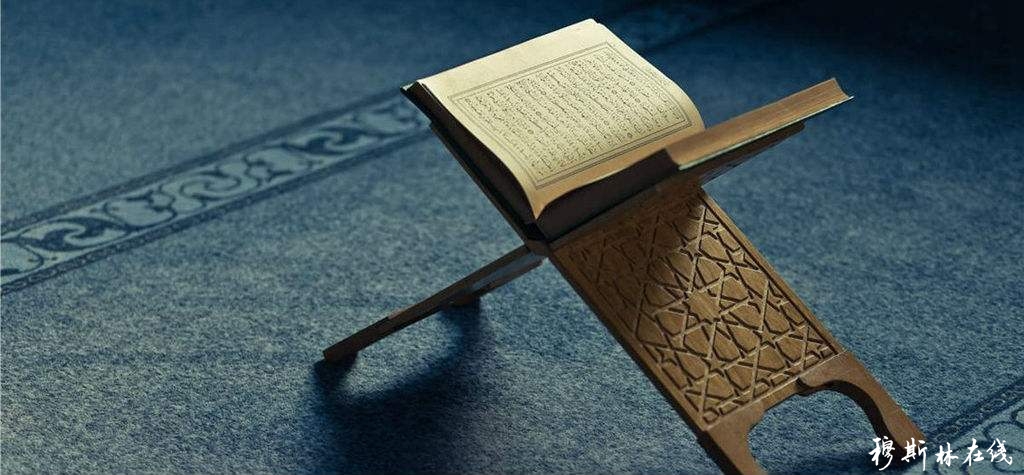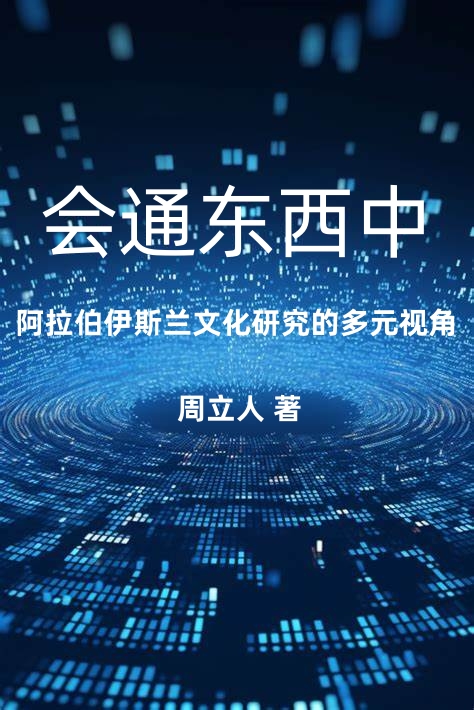二、中正美
伊斯兰美学的第二个核心内容是中正之美。《古兰经》说:“我(安拉)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2:143)的确,伊斯兰对于任何事物,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主张中和、适中的原则,即不可不及,也不可太过。对教义、教法、处理事务、待人接物、战争以及衣食住行等都提出中正之美的原则,反对偏激过度。《古兰经》说:“你们在拜中不要高声朗读,也不要低声默读,你们应当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17:110)“你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25:67)“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2:190)“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的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5:87)这一中正之美突出表现在它既肯定人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又告诫人们要控制各种世俗的物欲,切忌沉溺于现世的享乐而使人生目标迷乱——“你们可以吃我赏赐你们的佳美食品,但不可过分,以免应受我的谴责。谁应受我的谴责,谁必沦丧。”(20:81)
众所周知,物质生活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安拉说:“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地记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62:10)但人类的物质生产,包括生产方式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毕竟是有限的,而人的物欲则是无限的。伊斯兰中正之美的原则似乎从宗教的层面[1]解决了这一矛盾。它意在将人们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有效地控制在合理、合度的范围内,防止因物欲的扩张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人性的异化问题。
而早期的基督教神学以《圣经》所言“给人生命的是圣灵,肉体是无济于事的”[2]为依据,压抑人的合理欲望,结果出现了大量以禁欲主义为宗旨的修道院。后来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基督教开始走向禁欲主义的反面——尽管作为基督教神学之来源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也曾提倡过“中庸”之道。亚里士多德说:“善德就在于行中庸——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中庸——,行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能达到的中庸……既然大家已公认节制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予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中间境界(毋过毋不及)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3]
佛教则认为,人生之所以苦,其主要根源在于人的欲望,而要摆脱这种苦就必须从自身着手,通过修心禁欲的方式,达到一种灭谛[4]或涅槃的境界。佛教的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哲人的著作中也俯拾即是。譬如,佛教将人生的痛苦分为八种,其中有“求不得”之苦,近代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认为:“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决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与缺陷(即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5]他还认为,痛苦是经常的、持久的,因为痛苦不仅表现在需求和在追求需求满足的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阻力,而且还表现在一旦需求之物得到了满足,新的需求又会生成,从而产生新的痛苦。他说:一切痛苦都是“由于对自己的状况不满而产生的,所以一天不得满足就要痛苦一天,况且没有一次满足是持久的,每一次满足反而只是又一新的追求的起点。我们看到的追求挣扎都是到处受到多重阻碍的,到处在斗争中;因此,这种情况存在一天,追求挣扎也永远就要被看成痛苦,追求挣扎没有最后的目标,所以,痛苦也是无法衡量的,没有终止的。”[6]在叔本华看来,人最好还是不要出生,而已出生了的,最好设法返回到生命以前的状态,因为人生意味着无期的苦役。要得到永久的彻底的解脱,唯一有效的方法便是采取禁欲的生活方式。他将禁欲行为分为三种:一、放弃性欲。在他看来,肯定性欲即肯定生命和生命意志。而禁欲的第一步就是要否定体现生命意志的性欲。他说:“自愿的、彻底的不近女色是禁欲或否定生命意志的第一步。”[7]二、甘于苦行。苦行是一种折磨意志、压抑意志,使之无法实现自身目标的有效方法。它“表现于自愿的,故意造成的贫苦。”[8]三、死亡寂灭。死是对生命意志的彻底否定,只有“绝食而死”才是超脱痛苦的最终出路。他最后总结道:“美的美感那种怡悦的获得是由于我们摆脱了狠心的意志冲动,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的意志不只是在一些瞬间,如美感的享受,而是永远平静下来了,甚至完全寂灭,只剩下最后一点闪烁的微光维持这躯壳并且还要和这躯壳同归于尽,这个人的一生必然是如何的幸福。”[9]在这种如同小乘佛教“灰身灭智,捐形绝虑”的境界中,一切意欲断灭,因而也就无所谓痛苦。显然,叔本华的观点是悲观虚无的。他将彻底否定生命意志作为审美之最高标准也是荒诞离奇的。
当然,佛教也谈“中道”[10],但禁欲主义似乎始终是佛教(尤其是小乘佛教)人生哲学的主旋律。本无宗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即色宗坚持“色不自有,虽色而空”(《妙观章》);心无宗主张由空心达到空物:“心无者,无心于万物”(《肇论·不真空论》引)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以物欲为虚空、以涅槃为归宿的禁欲主义的色彩。而佛教所谓的“中道”既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且各学派对之解释不尽相同。小乘佛教一般以“八正道”为中道,据称按此修行,既能摆脱苦行,又能摆脱世俗贪爱。《中阿含经》卷五十六说:“舍此二边(指苦行和贪爱)有取中道成明成智成就于定,而得自在,趣智趣觉趣于涅槃,谓八正道。”《杂阿含经》卷十二等则将观悟十二因缘之理,弃舍常见(视人我常存不变)与断见(视死后全无果报)、有见(以世间为有)与无见(以世间为无)称为符合“中道”的正见。大乘中观学派称“八不缘起”为中道,大乘瑜伽学派则以“非空非有”为中道。
而在儒家看来,中正(即中庸)既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方式,又具有本体论及伦理学上的意义。例如,《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谓上天所赋予人的天性可称作从善的本性,依照而不违背这种本性去做事可称作中庸之道,修养和推行中庸之道可称作教化。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把中庸看作天地间最根本的法则。儒家认为,如果人人都按中和、中正的法则去做事,那么整个社会就和谐了——“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其表现为“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具体地说,就是天地、万物和人都达到一种相通的、完美的境界:“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
儒家还把遵循中庸之道看成是衡量君子的标准之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意思是:君子能做到中庸,是因为他具备了做君子的品德,同时为人处世时常讲究适中的原则。其具体表现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意思是:君子不但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而且还虚心请教他人,使自己的学识不断扩充以至尽知天底下精深细微之道理,最终达到最高明的精神境界,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意思是:与没有中庸之德的人交往,必然会遇到两种人,一种是言行激进,另一种是孤洁自守,前者贸然进取,后者无所作为。东汉时期的徐幹说:“君子之与人言也,使辞足以达其知虑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过其任而强牵制也。”(《中论·贵言》)意思是:君子和人言谈时,使自己的言辞在对方能够理解的范围内,所谈论的事情适合于对方的性情,不超出对方的承受限度而勉强为之。上述观点表明,儒家提倡上至修德求学,下至言谈举止都应该以中庸之道为旨趣。
然而,中庸之道中往往又隐藏着调和论。《论语》中充满了这种调和的悖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这句话堪称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调和。[11]后来,北宋的二程也学会了这种两端兼顾型的折中主义。例如,有人问程颢世界上有没有鬼神,他的回答似乎模棱两可,依违其说:“待说与贤道没有时,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说与贤道有时,又却恐贤问某寻。”(《二程集·遗书》卷三)有人问程颐如何解释“福善祸淫”[12]之类的现象,他曾否认这些是天神意志所使然:“且说皇天震怒,终不是人有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二程集·遗书》卷二十二)但又认为:“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世间有鬼神冯依言语者,盖屡见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二程集·遗书》卷二)
关于中庸之道所隐含的调和与折中,马中在《中国哲人的大思路》一书里以礼和仁作为例子,指出:礼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强调的是上贵下贱的社会等级,在政治上可以说是遵循着一条保守主义的路线,而仁作为一种内在的修养,立足于“仁者爱人”等道德目标,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孔子却巧妙地运用中庸之道调和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马中说:“在孔子的学说中,仁与礼未形成冲突,孔子以礼说仁,以仁说礼,以旧论新,以新论旧,仁与礼、新与旧浑然一体,难以厘清,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折中’状态(既不过于保守,亦不过于激进),这就是后来的保守者、革新者都援引孔子而又都不满于孔子的原因所在。”[13]他认为,在儒学礼与仁的结构中,礼与其说是辅佐中庸之德的手段,不如说是目的,而中庸之德却可以是服务于礼的,或者干脆等同于礼—— “在孔子看来,‘度于礼’就是‘事举其中’,执中与执礼原则上是一回事……中庸之德全面而深刻地奠基于礼治之中。”[14]后来,程朱理学则干脆把“中庸”当作“天理”或“天命”。程颢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集·遗书》卷七)“圣人以理为一,过犹不及,中而已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中庸章句》)
在评价中国文化所提倡的“中庸之道”时,萧兵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思想史中,“中庸是未完成的真理,待努力的理想。它既不是‘绝对’,又不是‘普遍’,还不是‘本源’。它只是中正平易的日常行事之道:愚者不及,智者过之;不肖者不及,贤者过之。但既是理想,就有其超越性,所以也要修炼、攀援,所以又是‘鲜能’的;而既然未完成,它就不是‘封闭性’,而永远不可穷竭,永远有望臻至。这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然而它的不彻底性、易扭曲性也就埋伏在‘不完美’之中,很可能从此走向自己的反面……而又由于‘中庸’本身这种经验性、庸常性或平易性,更由于中国人‘人本位’文化的务实趋善性、经世致用性,‘中庸’往往不能竭力去求索,臻至‘高明’而拘囿于自身,甚至违背着自身。迟滞、迂执、封闭,弄得‘既不中庸,又不高明’。重人轻物,重实轻虚,重内轻外,重行轻思……都不是‘度其两端而执其中’的中庸,遑论‘高明’……这样中国人就很难接受‘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的独立精神、自由原则,而因其追求利用厚生的‘短期效应’而丧失科学或真理自身的高明博厚,以及其固有的多元价值。中国哲学、逻辑学不够发育,中国科学、基础理论逐步走向落后、衰微,中庸之轴容易摆向偏狭的实用、庸凡的功利也是重要原因。”[15]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对中庸之道持保留态度,认为即使在中庸之道里面,也隐藏着偏执于一端的可能性。他说:“杨子取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意思是:杨子主张为我(即贵己),即使是只须拔去自己一根毫毛而有利于天下的事情,他都不愿意去做;墨子倡导兼爱,哪怕是摩秃头顶、走破足根,只要有利于天下的事,他都会去做;子莫则采取折中的态度,这样虽然近乎事理,但如若不能很好地权衡利弊,把握好分寸,那就跟偏执于一端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之所以反对偏执于一端,是因为这样做有损于常道,是因为这样做只顾及了一端而不计其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庸之道在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的手里竟然演变成一种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他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庄子·秋水》)这里所说的“道”既指大道、常道,也指中庸之道。“明于权”指懂得和善于使用权变之术。《庄子·山木》记载的一则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繁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也就是说,有用和无用都可能给自己带来危害,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蛰伏,既不要太锋芒毕露,也不要太自轻自贱,该当龙时就当龙,该当蛇时就当蛇,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即所谓“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庄子·山木》)
这说明,客观真理在具体的实践中总会出现偏差或者变异,因为作为客观真理之推行的人,其主观意志、情感和价值观等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杂到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即便是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大家知道,“伊斯兰教是反对饮酒的,对酗酒更是明令禁止。真主降下一节经文:‘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恶魔惟愿你们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仇恨,并且阻止你们记念真主,和谨守拜功。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博)吗﹖’(5:90-91)尽管有这节经文,但围绕高尚的经文又引出许多问题。如酒的含义是什么?仅仅是指葡萄汁,还是一切醉人的东西?禁酒的限量是多少?是对一切种类的酒不管多少都禁,还是允许少量地饮用某些种类的酒?……不同的意见在圣门弟子时代就出现了,以后又一直争论不休。到了几位大教长的时代,旧的分歧又重新出现了。三位大教长——马立克、沙斐仪和罕百里断然关上了饮酒的大门,把前面引用的《古兰经》经文解释为禁止一切醉人的色酒,包括椰枣酒、干葡萄酒、大麦酒、玉米酒、蜂蜜酒等。他们说,所有这些都叫酒,都在被禁之列。而大教长哈尼法则根据字义把这节经文中的‘酒’解释为葡萄汁。这一创制导致了允许饮用某几种色酒,如椰枣酒和干葡萄酒,但必须是新近制作的,而且只能少量饮用,以不醉为限。”[16]
[1] 在现实生活的层面,由于各人的价值观念不同,对“不可过分”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因而在阿拔斯王朝初期,曾出现享乐、严肃和苦行三种生活方式并存的局面。从曼苏尔、迈赫迪、拉希德到艾敏,这四代哈里发的生活方式也有着极大的差异。
[2]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第63节,引自《圣经》(现代中文译本), 香港圣经公会出1979版,第156页。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4-205页。
[4] 佛教有“四谛”之说,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按佛经解,“谛”乃真理之意,苦谛是讲人生的种种痛苦现象,如生老病死、怨憎别离、求不得等;集谛是讲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如“业”和“惑”;灭谛是讲断灭世俗诸苦得以产生的根源;道谛是讲实现佛教理想境界(灭谛或涅槃)的有效途径。
[5]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7页。
[6]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4页。
[7]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1页。
[8]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3页。
[9]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35页。
[10] 佛教所说的“中道”,即离开两边之极端、邪执,也就是不偏执于对立面的任何一方之中正之道,又称作“中路”,或单称中。中道系佛教之根本立场,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所重视。
[11] 歌德曾经说过:“一位思想家的最大快乐在于已对可知的事物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而对不可知的事物敬而远之。”见Goethe, Maxims and Reflections, Hermann Weigand (ed.),Pantheon, New York,1949, p.4。 假设孔子没有诸多的有神论的观点,那么,“敬鬼神而远之”也可以看成是无神论的观点。但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孔子只是出于维护孝道才没放弃“鬼神”的观念。
[12] “福善祸淫”:《古文尚书·汤诰》上说:“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13] 马中:《中国哲人的大思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508页。
[14] 马中:《中国哲人的大思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513页。
[15] 萧兵:《“中国”之名,“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为什么能持久?——中国思想史单元研究的初步尝试》,《淮阴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16]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90版,第10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