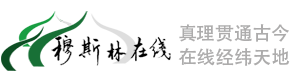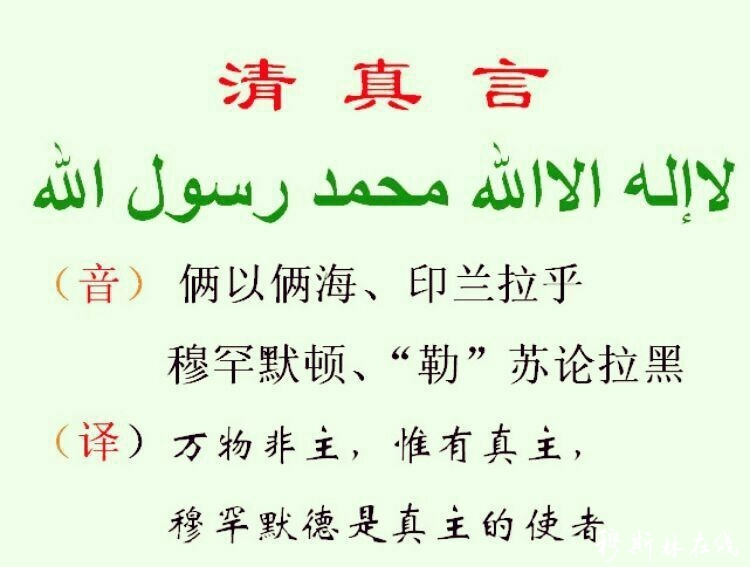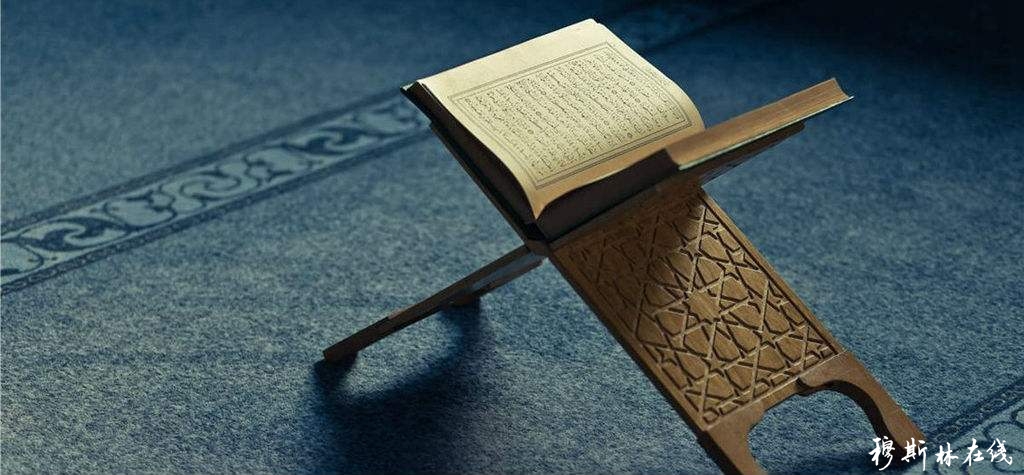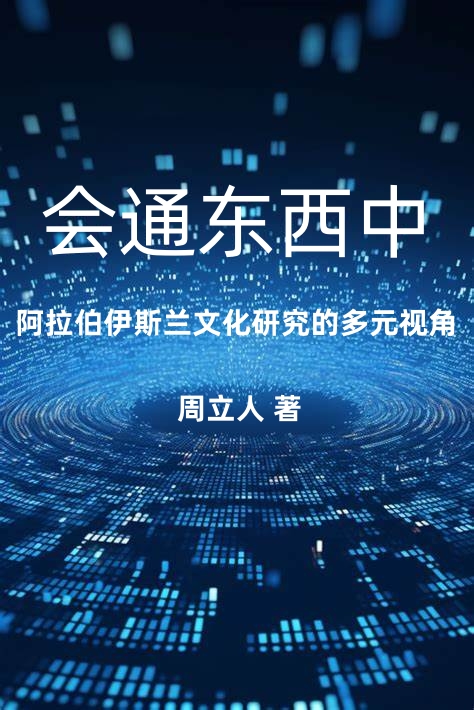一、和谐美
伊斯兰美学首先强调“认主独一”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安拉创造的。“他(安拉)在六日之中创造了天地万物。”(11:7)[1]“他是创造昼夜和日月的,天体运行各循一条轨道。”(21:33)“他使黑夜侵入白昼,使白昼侵入黑夜;他制服日月,各自运行至一定期。”(35:13)“他为你们创造诸星,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的重重黑暗里借诸星遵循正道。”(6:97)“他从云中降下雨水,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长出翠绿的枝叶,结出累累的果实。”(6:99)他“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24:45)
伊斯兰认为,安拉本身就是美的最高形式和体现。安拉在造化自然万象的同时也赋予它们以美的内在逻辑和意义。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伊斯兰阿拔斯王朝中期的诗人,如赛纳尔伯利,在歌颂大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寄托了对造物主安拉的敬仰与赞叹:
人间惟有春色丽,
百花争艳醉人情,
天似珍珠地如翠,
万物披绿水作镜,
雨云飞空银丝洒,
大地含笑百鸟鸣。[2]
在伊斯兰看来,安拉既是美的创造者,又是美的体现者。不断寻求和发现事物内在的美及其意义,并由此体悟安拉的存在和他的大智大能,从而坚定自己的信仰,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
的确,美的内在逻辑和意义存在并始终贯穿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一切事物之中,大到宇宙天地,小到细胞粒子。从宏观的宇宙来看,无数天体按照自然定律井然有序地运行,勾勒出一幅令人神往的壮观场面。对此,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深有感触地说:宇宙间的一切都受同一自然规律的支配,日月星辰的运行是多么的庄严,这无疑使“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3]进化论者达尔文也说,展现在人类面前的宏伟而奇异的宇宙(包括我们这些有意识的人在内)绝不是偶然出现的,认为它是偶然出现的观点是难以令人折服的。牛顿则讲得更明确,他说,美丽无比的恒星、行星和慧星体系只能藉一位大智大能的存在体而存在,这个存在体永远不灭、无所不在,从而构成了宇宙的时间和空间。他还说:“行星按照轨道切线方向的运动,是在很久以前受到某种外来的‘第一次推动’而开始的,自那时起行星才围绕中央星球旋转,并会一直按同一方向旋转下去。”[4]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也认为,宇宙确乎是全能者意志的杰作,否认其存在就等于亵渎人类已拥有的一切知识。所有这些论述,从某种意义说都体现了科学家对宇宙万物背后力量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敬畏。
根据《古兰经》的描述,从人类居住的地球来看,安拉“从云中降下雨水,你们可以用作饮料,你们赖以放牧的树木因之而生长,他为你们而生产庄稼、油橄榄、椰枣、葡萄和各种果实。”(16:10-11)“他创造了牲畜,你们可以其毛和皮御寒,可以其乳和肉充饥,还有许多益处。”(16:5)“他创造马、骡、驴,以供你们骑乘,以作你们的装饰。”(16:8)“他制服海洋,以便你们渔取其中的鲜肉,做你们的食品;或采取其中的珠宝,做你们的装饰。”(16:14)“他为你们制服船舶,以便它们奉他的命令而航行海中。”(14:32)从微观世界来看,“我(安拉)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然后,我使他变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块,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23:12-14)“他(安拉)从无生物中造出生物,从生物中造出无生物。”(6:95)
这种宇宙自然的和谐美折射出伊斯兰宇宙统一性原理的智慧之光。在更深层的社会学与伦理学意义上,这一原理还同时要求人们在人与安拉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在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也建构起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准则,一种互动关联的、欢愉向上的美的宏观结构。
而基督教神学首先坚持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统一和谐论,并将“圣子”耶稣基督的受难视作“美”(悲剧美)的崇高境界。打开欧洲中世纪艺术史,我们可以看到科隆大教堂里的一尊《耶稣受难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瘦如枯柴、身心俱摧。这是表现耶稣受难的最早的艺术品之一。当时的欧洲人大都认为,将耶稣的四肢和腰部的五处伤痕复现于男女活人身上是一种神赐的圣物。狂热的信徒甚至在大庭广众面前自我鞭笞以示赎罪,同时也让人们身临其境般地体验耶酥受难时的情景,让一些情感脆弱的人挤出几滴眼泪。这种用毁坏自身体形来洗涤“原罪”的做法,似乎破坏了人与神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也破坏了灵与肉之间的和谐关系。[5]
《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夏多布里昂曾经说过:在艺术创造中,基督教“赋予思想以精力,献给作家以高贵的形式,献给美术家以完美的模型。”[6] “基督教让信徒淌出的一滴泪水里所包含的妙景,就比神话的全部逗人喜欢的谬误中所包含的还多。”[7]在论及自己和浪漫主义诗人斯达尔夫人的差别时,夏多布里昂说:“我的癖好是看到耶酥基督无处不在,就跟斯达尔夫人看到完美的可能性无处不在一样。”[8] 夏多布里昂的这些言论对我们解读基督教美学所推崇的以耶酥受难为主题的“悲剧美”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耶稣受难像》(它在某种意义上能唤起图腾崇拜的悲剧感和崇高感)和信徒的自我鞭笞(相当于原始人用石刀、石针等工具在身体的各种特定部位切划、黥纹),能营造一种可以净化灵魂的情感氛围。在这一带有明显原始宗教色彩的祭奠中,生命意志因痛苦和折磨而得到贬抑和否弃,追求与神同一或同在的情感得到抒发和满足。而基督教“赎罪”的主题也在这伟大而又神秘的祭奠仪式中得以永存。正如朱狄指出的:“艺术总是一种情感的产物,情感活动常常在赎罪仪式中就已经开始了。”[9]
这种试图在肉体的玉碎之美中求得灵魂的升华,在自我亵渎,自我摧残的悲壮音符中求得理性张扬的信念,实际上或多或少地也散见于西方某些哲人的美学理论中。例如,在西方美学思想史上,苏格拉底首次将人的存在划分为两个部分:肉体的存在和灵魂的存在。他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羁绊,而灵魂则是肉体的主宰,肉体和灵魂永远处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他说,一个人如果想追求灵魂的善与美,就必须彻底摆脱肉体的纠缠。“人只有解脱了肉体的愚蠢之后,才能变成纯洁的,才会知道到处都是光明,而这种光明不是别的,乃是真理之光。”[10] 显然,苏格拉底推崇的是灵魂与肉体分离之后所形成的“纯洁”之美。德谟克利特则认为,美感具有两种形式:肉体的快感和灵魂的趋善;前者纯属感官上的享受,后者属精神上的净化。他说:“凡期望灵魂的善的人,是追求某种神圣的东西,而寻求肉体快乐的人则只有一种容易幻灭的好处。”[11]柏拉图以所谓崇高永恒的美——“理念”压制一切与感性相关的情欲,将肉体感受性贬为人性中黑暗的“低劣部分”。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通过集体生活的制度、措施和法律来限制和压抑个人的自由、个性的权利。”[12]亚里士多德则把情欲本能归于灵魂中较低级的“非理智因素”,他认为,灵魂不但要统治肉体,而且还要用理性去克服“非理智因素”。他还将精神方面的享受看成能唤起人们愉悦之感的美。他说:“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为不仅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幸福正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结合。”[13]
除了借助以“受难”为主旨的赎罪仪式来损坏灵与肉的和谐关系外,基督教神学似乎还以类似“拜物教”的方式打破了创造者和被创造者之间的和谐秩序。爱德华· 詹姆士·马丁在《神像破坏运动史》中写道:“当尼西亚理事会于787年聚会,准备彻底解决神像问题时,基督教神学在神像问题上的系统阐述已达到极度自由的状态:‘我们按照正统的方法和神灵激发的教义,准确无误地断定:价值连城的救生十字架、神像、绘画、马赛克(即镶嵌砖)和其他装饰材料都应当出现在神圣的教堂上,衣服、悬挂物、宗教器皿等物品上也应有类似的装饰。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描绘我们的上帝、教主耶稣基督,描绘圣母、天使、圣人和所有虔诚者,因为人们经常在绘画中目睹他们的尊容,便能纪念他们、渴望见到他们,便能向他们表示敬仰之情。这样,人们便不至于盲目崇拜仅属于神性的东西,而是衷心崇拜价值连城的救生十字架、福音书和其他物。而且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按照古老的虔诚习俗,向神敬奉香火。由于可以把对神像的敬仰通过神像转到神像体现的神身上,因此,我们圣父的教诲便能得到加强。’”[14]他还指出:“除了描绘官方规定的形象外,东正教还培育异教艺术,推崇古希腊人的主题和亚历山大的东西。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著名哲人外,一些文人作家,如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和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也先后加入了圣人和使者行列。总之,他们把盲目崇拜看成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导致盲目崇拜者把创造者和被创造者彼此颠倒。”[15]
而彻底否认造物主存在的佛教,则往往把现世的一切看作折磨人的苦役,因而佛教美学表现的是远离人生、超脱现实的主题。雕塑于南北朝时期的我国龙门石窟等地的一些佛像,大都表现出看透人世间一切,寄希望于断灭“因缘”和断灭“轮回”的神态。佛教艺术还根据佛经上的传说塑造过去佛燃灯[16],现世佛释迦和未来佛弥勒[17]。其中,弥勒佛像不是敛容正色,望之俨然(如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交脚弥勒佛),就是嬉皮笑脸、大腹便便(如五子戏弥勒佛像)。这种“出世”和“入世”的对峙(而不是统一和谐)从一个侧面证明佛教美学和佛学的内在矛盾。事实上,佛教具有“外尚无相,内尚无知”的反美学特征。“无相”论认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相这四相皆由眼根而来,是人的烦恼的起因。《金刚经》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相,即非菩萨。”其重要命题是“色即是空”。美作为相色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是空的,审美对象因此应当予以否定。而由“无相”产生的“般若”之智的特点是“无知”,即超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从而达到无上正觉。因此,审美感受乃至包含这种感受的审美主体也应当统统予以否定。然而,虽然佛教由“无相”“般若”否定经验世界的美,但又认为,一味彻底否定世俗美也是一种“有”,而且是一种带有执着和偏持一边的“有”,真正的“无相”、“般若”应该连这种否定也给否定掉。于是,佛教就从“非美”走向了“非‘非美’”(也就是由“色即是空”转为“空即是色”)。结果产生了大量的佛教艺术,“借微言以津道,托形象以传真。”[18]
这种从“非美”走向“非‘非美’”的过程,或许是受了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创始人龙树的佛学理论的影响。在谈到万物缘起时,龙树主张“破执空有”,认为缘起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空,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有。他提出“八不缘起”说,即“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中论·观因缘品》)在轮及真假二谛时,他主张既要看到现象的性空,又要看到现象的假有。后秦僧人鸠摩罗什继承了龙树的中观论,提出“空有迭用”的见解。鸠摩罗什说:“佛法有两种。一者有,一者空。若常在有,则累于想著;若常观空,则舍于善本。”(僧肇《注维摩诘经》卷六)隋朝时期,三论宗代表人物吉藏则主张“空有相依”。他在《三论玄义》中说:“有不自有,因空故有;空不自空,因有故空。”
当然,儒道佛三家也谈“和谐”之美:儒家着眼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追求的是人与人的和谐;道家着眼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着眼于心物关系和因缘关系,追求的是人自身内部的和谐。
为了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孔子倡导周礼与诗乐相统一的美学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还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在他看来,社会规范和仁义道德的维系要依靠诗乐这些艺术形式的力量,因为它们能够在陶冶人的情操的同时,唤起他们趋善避恶之心。道、德、仁、艺合而为一才能最终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实现天下大治。这种强调艺术为伦理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看是积极的。但孔子的美学思想因受其恢复和维护周礼的功利主义心态的制约,具有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
为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提倡遁世哲学,反对文明,鄙视伦理。他对自己所追求的精神放逐般的境界描写道:“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咳;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老子·第二十章》)意谓世人是那样的快乐,就像是在享用盛宴上的美食或者像登上春意簇集的楼台观赏景色,惟独我过着淡泊无为的生活,就像刚出世不久的婴儿还不会笑;我身心疲惫,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世人都富足有余,惟独有所丢失。而庄子在继承老子自然主义学说的同时,醉心于“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即所谓“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 (《庄子·大宗师》)。庄子的这种超越人生的美,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浓厚诗意色彩的浪漫主义的理想。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便是用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与自然的交流和某种怀旧情绪)来表现无限。在浪漫主义者那里,人生往往被涂上了一层如梦似幻的美的色彩;一种非理性化的对永恒与自由的眷恋通常是用来张扬个性,贬抑共性的。倘若从这一视角来解读老子,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对自然的崇尚和对“小国寡民”社会形态的偏爱(个性),对社会和文明(共性)的反感与反叛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浪漫主义的倾向。如果说19世纪约翰· 马丁的《吟游诗人》[19]为我们了解近代西方浪漫主义关于“人、自然、社会”的思想提供了一把钥匙,那么,带有浓厚吟游诗人气质的老子早在2500年前就开始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诸关系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了。如果说庄子的浪漫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表现出来的无奈和聊以自慰,那么,老子的浪漫主义则更多地带有一点伤感和怀疑主义的色彩。
为了达到人自身内部的和谐,佛教也不乏浪漫主义的情结,如《观无量寿经》中载有十六种想观,即日想观、水想观、地想观、树想观、莲花想观等。所想所观的对象,当然是自然界的造物。也就是说,佛教也试图通过与自然的交流达到净化灵魂、保持身心高度统一的目的。除了想观外,佛教还强调直觉和顿悟,认为“非悟无以入其妙”,并且主张用佛法上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来净除心识上的六蔽(贪婪、妄为、瞋恚、放逸、散乱、愚痴),以达到佛性[20]复归的境界。在佛教看来,一切众生原本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佛性),但因妄想执著[21]而不能证得,以致起祸造业,轮回六道。《大乘义章》曰:“凡夫迷实之心,起诸法相,执相施名,依名取相,所取不实,故曰妄想。”这种妄想执著又称无明(意为“暗钝之心”),它和原本灵明寂照的智慧德相和合在一起,相续相牵、熏习不已,便成了所谓“阿赖耶识”(即染净交参的心识)。而为了求得人自身内部的和谐(在佛教看来就是回归人原始清净纯真的本性)就必须彻底剔除妄想执著,灭小我而进大我。
[1]《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165页。本章所引《古兰经》节文均出自该书。
[2] 转引自蔡伟良、周顺贤《阿拉伯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3] 爱因斯坦:《我的信仰》,《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182页。
[4] 引自刘蔚华主编的《世界哲学家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版,第792页。
[5] 参阅樊锦鑫《灵与肉:耶稣受难像随记》,《美育》1988年第3期。
[6]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卷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7]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卷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8] 引自保尔·第根《导言》,见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9]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07页。
[10] 引自张步仁《西方人学发展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
[11] 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第107页。
[12] 张步仁:《西方人学发展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1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14] Edward James Martin, A History of Iconoclastic Movement, London,1967, p.33.
[15] Edward James Martin, A History of Iconoclastic Movement, London,1967, p.33.
[16] 燃灯,也译作“燃灯佛”、“锭光佛”。《大智度论》卷九说,燃灯佛在他降生时,周身光明若灯火。《瑞应本起经》载:释迦牟尼前世曾买五茎莲花供献该佛,故被受记(预言)九十一劫后之“此贤劫”时当成佛。
[17] 弥勒:佛教菩萨名。佛教传说,他将继承释迦佛位为未来佛。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载,弥勒出生于婆罗门家庭,后为佛弟子,上生于兜率天内院,下生于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修成正觉。
[18] 参阅王海林《佛教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和高长江《禅宗与艺术审美》,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 约翰· 马丁的画《吟游诗人》1817年首次在伦敦展出,其题材取自托马斯· 格雷的一首诗,该诗叙述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对威尔士的征服以及迫害当地的吟游诗人等重大历史事件。画面上充满了浪漫主义作品所特有的神秘感和无限感。人们可以从背景中的城堡以及吟游诗人与山顶上看不见的东西的交谈感受到吟游诗人对中世纪和大自然的眷顾。
[20] 佛性又称觉性、如来性、真如实相、常住佛性等。本指佛陀本性,后泛指人排除了空性后跟佛陀一般的灵明洞彻、湛寂常恒的本性。《大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性论》卷二谓有三种佛性:一、自性住佛性(众生先天就具备的佛性);二、引出佛性(由修行引发的佛性);三、至得佛性(达到佛果时本有佛性得以圆满显现)。
[21] 执著:即“执着”之意,指专注于人世间事物而不能求得超脱或者指偏执于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