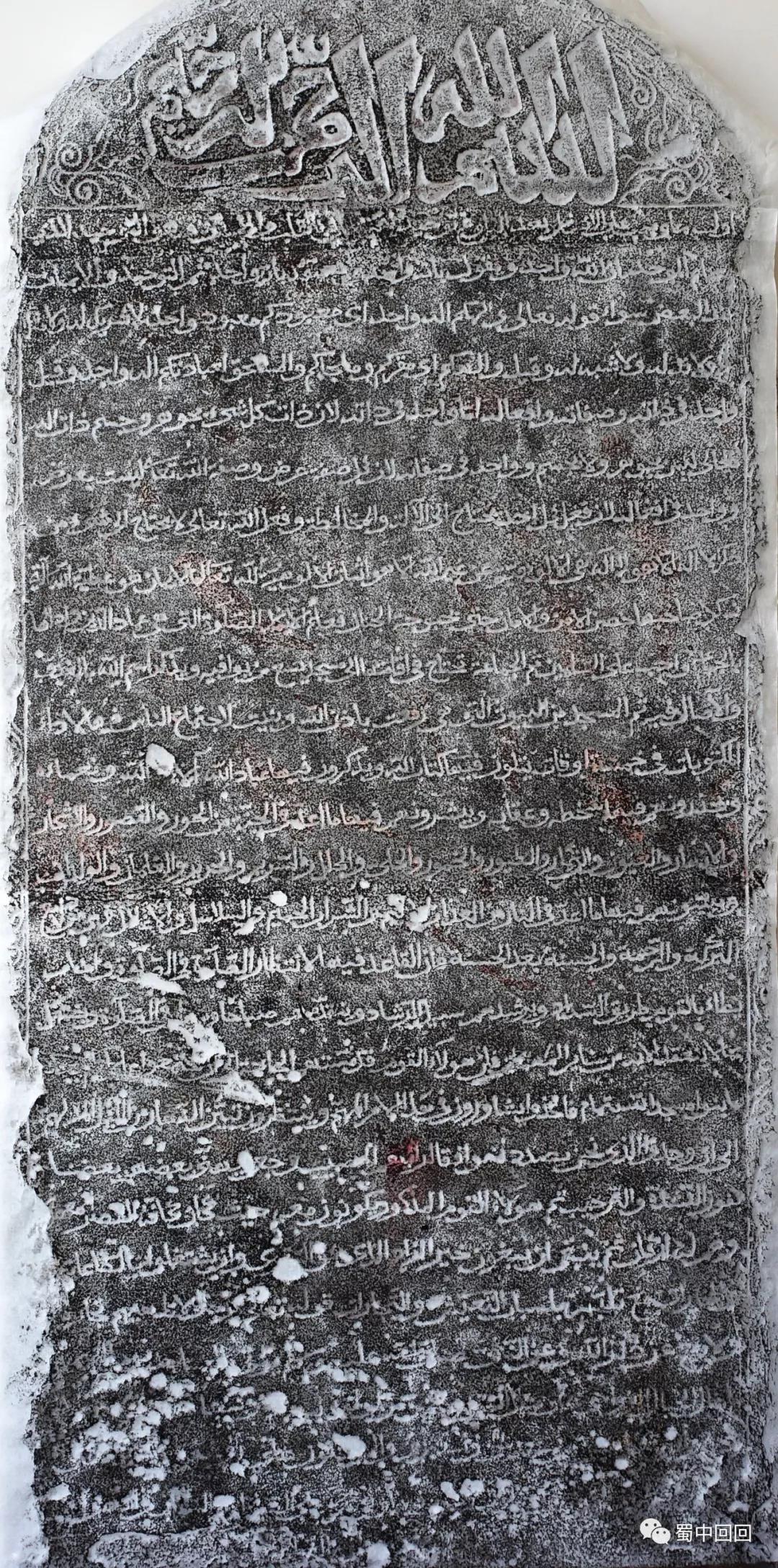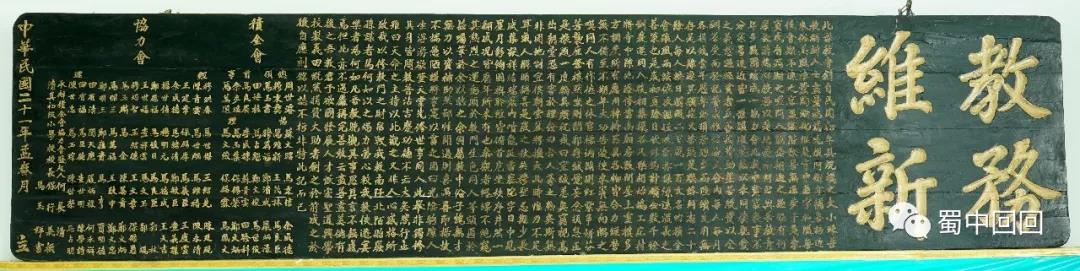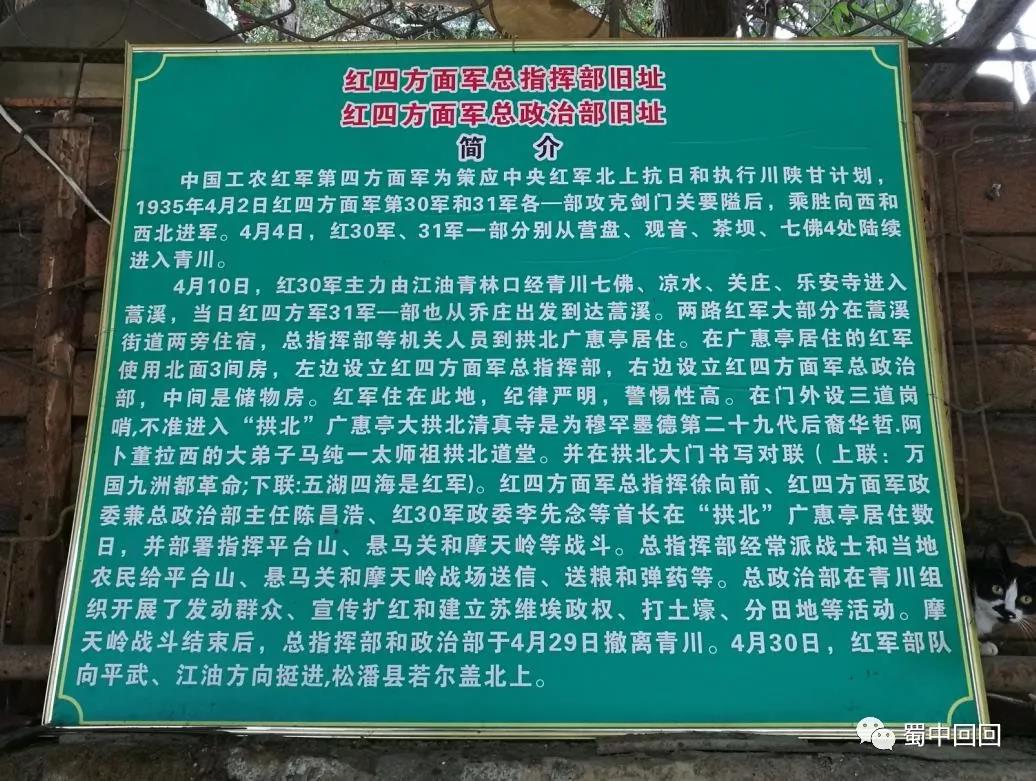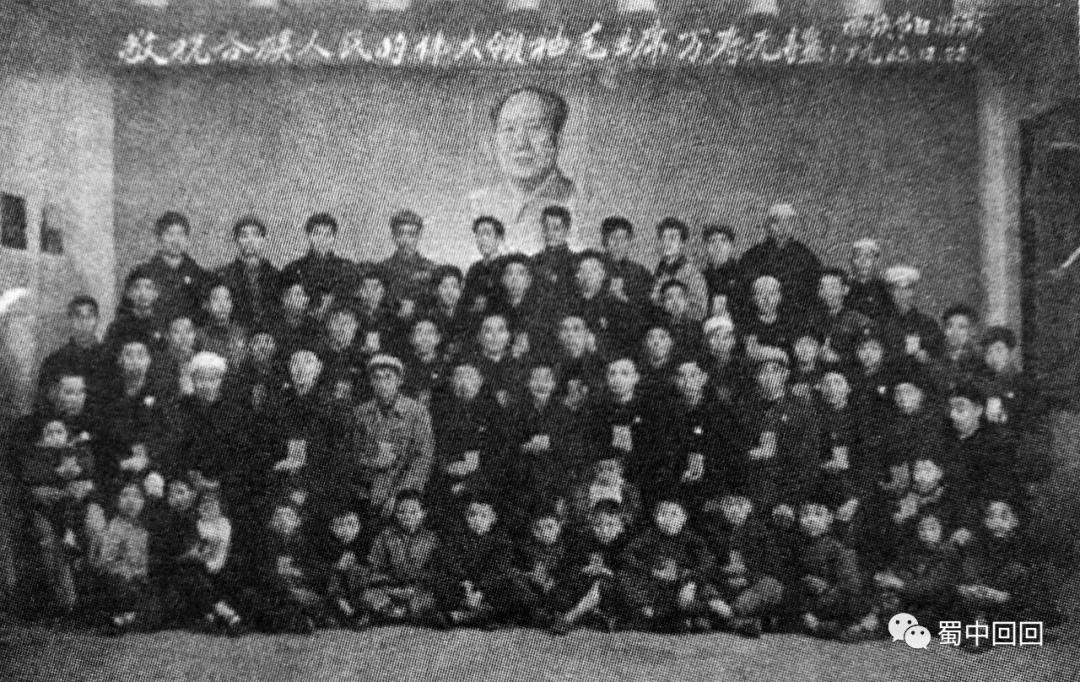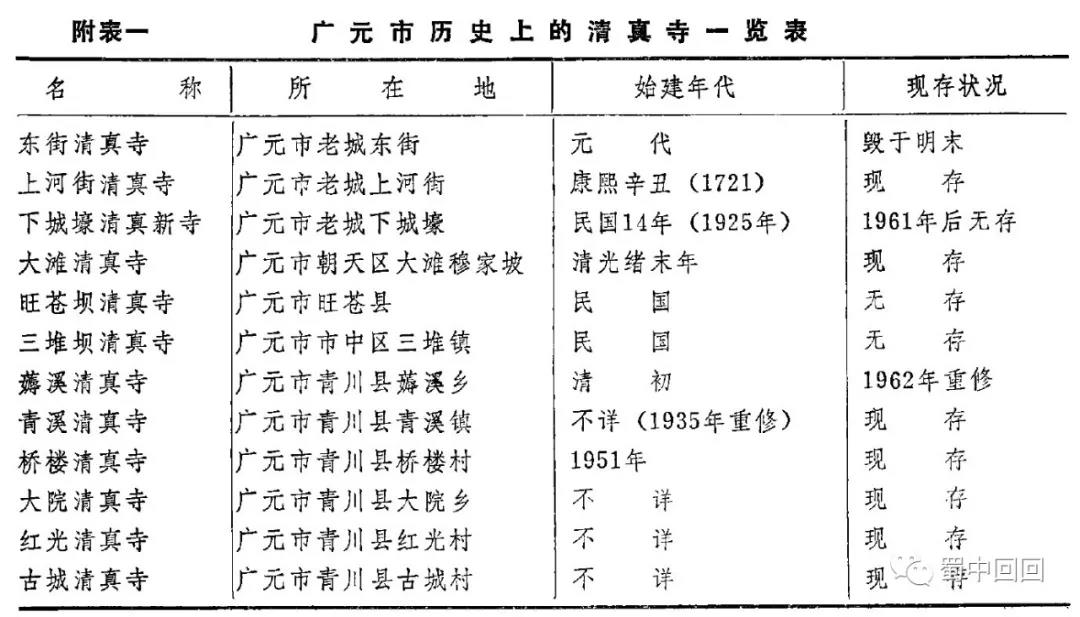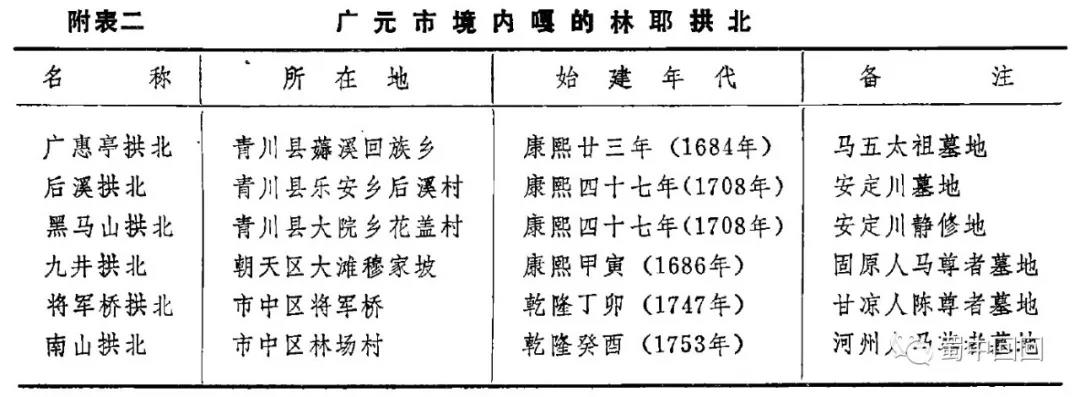|
周传斌
简介: 周传斌( 1972— ) ,男( 回族) ,山东平邑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民族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和伊斯兰文化研究。
热门排行
|
周传斌:广元伊斯兰教考略
【按:本文作者周传斌,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作者曾于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读本科期间,到四川省广元市进行田野调查实习,本文即作者实习期的研究成果。本文最初发表于《回族研究》1996年第4期,现经作者授权,本公号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同时,也通过分享此文,对周传斌教授在四川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方面的研究表示感谢!】 上一篇:“去中国化”误读: 以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为中心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