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人的林松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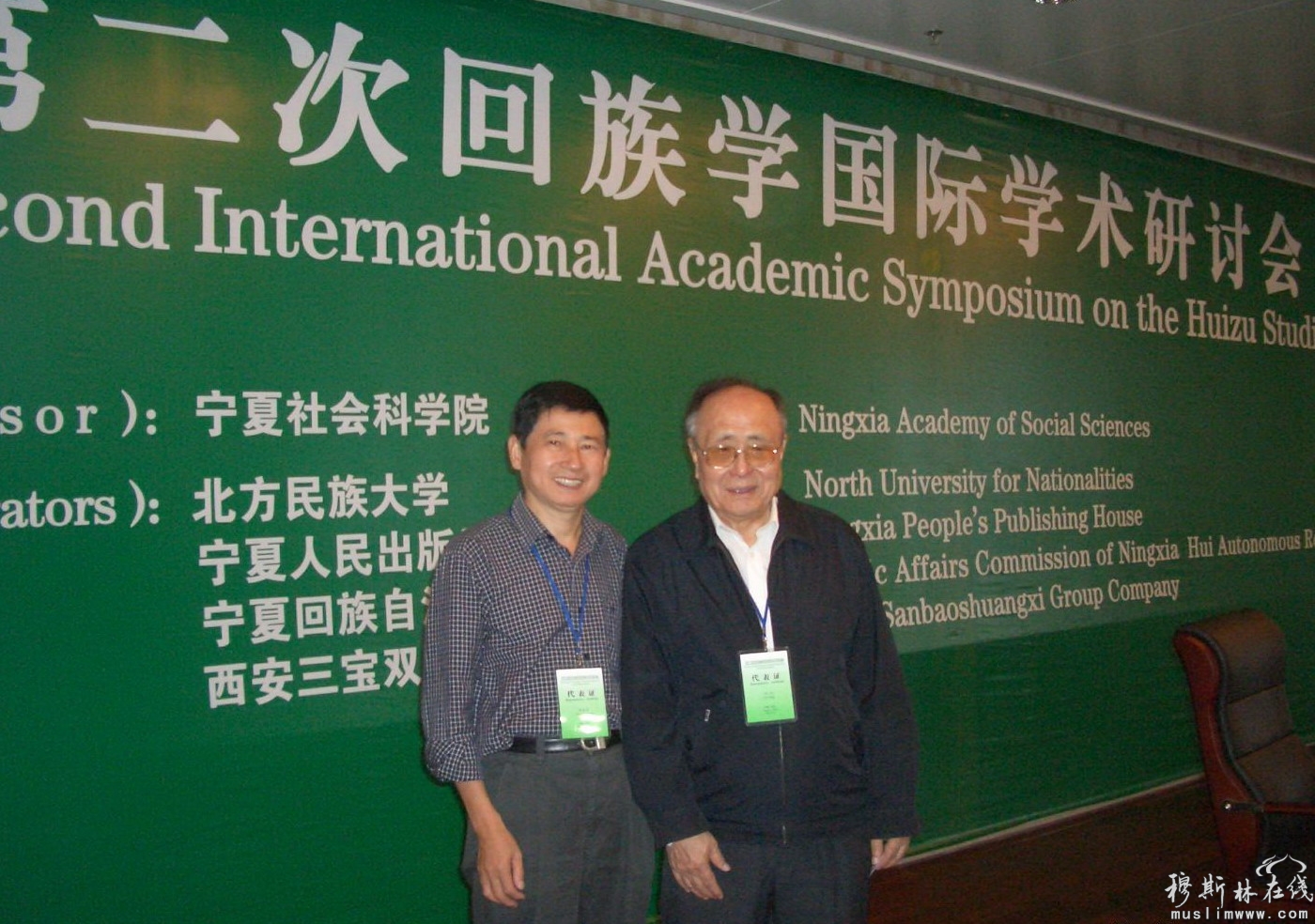
有道是“以文会友”。自从我爱上回族伊斯兰教地方史的研究后,就有幸认识了不少当代回族史学的专家学者,如林松、马寿千、杨怀中、马启成、郑勉之、李华英、李松茂、冯今源、杨大业、姚继德等。德高望重的民族史专家,个个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和林松教授是1983年在西安认识的,那一次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研讨会上,我拿着我的习作《嘉兴清真寺今昔》,第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结识林老,还要感谢《中国建设》阿拉伯文版主任程德淦先生。程老祖籍嘉兴,是个在中东采访多年的汉族老记者。他来故乡采访嘉兴回族时,我全程陪同。后来他去埃及采访,又认识了当时在埃及工作的舍弟全美。程老也参加了西安会议。热情的他,不但事先告诉我,要拜访哪些人,还亲自领着我到林松教授的房间里。我才初中文化程度,去见大学者,心里确实有些自卑。一进西安大厦林老的房间,林老随和地问了我是哪里人,什么工作等等。家常话一下子消除了我战战兢兢的心理。程老介绍了我正学习地方回族史的情况,还硬让我当场给林老背诵“法蒂哈”。我红着脸,速度极快地背完了,谈不上音正腔圆。林老听罢又问:“还会啥?”我答:“几个‘索勒’”。林教授热情地鼓励了我一番。从那以后,我一个初涉民族史的晚辈和大名鼎鼎的林老开始了联系。1990年,林老在出席江苏太仓召开的郑和研讨会前,携夫人纳锦文老师来嘉兴访问。他们参观了清真寺,礼了拜,走访了几户回族人家,还游览了南胡。家父当时在上海小桃园寺任教。家母和我陪同他们参观了乌镇茅盾故居,石门丰子恺故居。茅盾、丰子恺先生,林老都认识,他说丰子恺先生是他的老师。林老饶有兴趣地观看展览,还为我们充当讲解员,言谈中充满了对大师的尊敬。十多年后他还跟我提到这次“舒畅开心”的旅行。
我们的联系也有过中断。那是我更换住址没及时禀报他。林老1995年10月24日来信称:“近年来,一直为寻觅你的地址而大伤脑筋。接你四月底来函地址,因有所求而及时复函,却被无情地退回了。尽管也写上了来函信封上的邮编号码。为此,到处打听。我真在八月份新疆出席第八次回族史讨论会时还把这退回的信封带上,以为你会去开会。不料此会连米寿江、郑勉之等可能知你近况的人也未去。”不说当时拜读该信的感动、亏欠心情,如今撰写文稿,敲打这段文字,不禁眼眶湿漉漉的。我是马大哈,对数字迟钝,特别容易忘。2007年1月19日林老发来手机短信:“久无联系,最近好吗?”我短信回复,大意是“我正在温州,进行回族社会调查。您是谁?对不起,我忘了这个号码。”我真混啊!竟连林老的手机号码都忘了!林老长我19岁,见面称呼:我称“林老”,他叫“成美”。书信中,我加上“尊敬的”三字。他却写“尊敬的成美朵斯梯”、“尊敬的成美老弟”等。林老馈赠我一套他的译作《韵译古兰经》(上下)。他在扉页上,用中文阿拉伯文题曰:“成美教兄惠存,并乞对拙译指缪。林松敬赠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成美贤伉俪惠存,并祈教正拙劣译句。林松、纳锦文敬赠于北京。”当初看后,顿觉诚惶诚恐,实在不敢当。这不折杀了我吗?同时我也领略到了大师的谦逊,感受到了林老的亲情。现在的心情,实说实话,能傍上林老这样的名家,自感很荣耀,心里确是暖洋洋的。我俩的交谊,以前我极少向外透露,近年偶尔也炫耀显摆一下。2006年9月24日有“普天同庆莱麦丹,喜迎斋月祈平安。林松”的手机短信发来,我让坊上张阿訇看了。他啧啧称奇,叫我马上把短信转到他手机上。林老在基层回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2006年春,我、浙江衢州伊协马杭清会长和义乌清真大寺马春贞阿訇商量,邀请林老和李华英老师来义乌访问,和浙江穆斯林见见面。二老因“年事渐高,远游困难”,未能成行。我们惋惜不已,徒唤奈何!不过浙省各坊的社首不放弃,正在酝酿召开学术研讨会,盼望林老等各位专家学者届时光临。
人们夸赞辛苦,常用“日理万机”;形容繁忙,爱用“百忙”。请看林老咋忙的?我看跟谁比较,都逊色不到哪儿去。林老长期伏案写作,精力、体力不支,1994年因忙于赶一个限期完成的课题,终究不可勉强,中途犯病住院,还是延误了日期。林老告诉我,1994年到1995年6月,“粗略统计一下,至少有520封信积压,内心沉痛。尤其是有几封急待回答的陌生朋友的信件。”追逐明星、结识名家乃当今时髦。可以想像信件的内容,有慕名信访的,有探讨学术的,有寻找知识的,有告急求救的,有要求序跋、签名题字的,等等。这名人真不好当啊!我不禁也替林老犯难了。林老勤于笔耕,每年有新作发表,加上各种会议、数百封信的应酬,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我这里敬告还未收到林老回信的朋友,别抱怨老人,他实在是忙啊!2003年我途径北京,在舍弟全美家住了3天,我在京城消息没告诉林老,也没去林府拜访。敬畏?自卑?怕打扰他?兼而有之吧!我说不清,道不白。
林老著作等身。我最早接触的,是他关于航海家郑和的两篇大作:《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奉佛、崇道说》(《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1、2期)和《从回回民族特殊心里意识综观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性》(《回族研究》创刊号、1991年)。记得八十年代初,学术界在议论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时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极左影响尚存。林老既有识又有胆,发表高见。我当初阅后,觉得在理;论文题目的字数均20以上,特长,印象亦深。林老两文及稍后的专论,对于正本清源、厘清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我看到了一个坦荡无畏的学者。又记得1999年底在北京小汤山,林老问一位会议代表的住址、邮编等,随即输入计算器。那年他已69岁。林老接受新事物特快,真酷!我眼前是一位勤奋好学的长者。我初中学的俄罗斯语,荒废几十年,除了“谢谢”、“起立”、“再见”几个词,全还给老师了。英文一点不懂。1999年,我还不会电脑打字。我想林老古稀之年熟练打字操纵计算器,自己也不能落伍。后来我努力学会了打字。现在写文稿,都是自己在电脑上慢慢打的。前年,林老已能群发短信,我至今还不会呢!还记得小汤山会议正逢斋月,我也没打听如何封斋的事。第二天晚饭,林老、敏生光教长他们好几个人一桌,在一起吃开斋饭。我脸红了,挺难为情的,不敢正眼瞧看他们。当夜我也起斋了,和我同屋的国务院某部门的回族老干部挺支持的,一点也不嫌我打扰了他。我觉得林老是个真正的穆斯林。林老夫人纳锦文老师,也是云南人。个子不高,和蔼可亲,说话轻轻的。纳老不但管好后勤,辅助林老做帮手,而且自己也收集资料撰写文章,我曾看到过。
每次见面,林老总是支持我钻研回族伊斯兰教文史。这方面,他讲的话虽不多,但要点明确。我记忆最深的是“尽可能的占有第一手资料。”我遵照林老的教导,跑遍了浙江各个清真寺,搜集碑刻;翻阅浙江各地方志,查找史料。在《中国穆斯林》、《回族研究》、《伊斯兰文化研究》(西安)等发表二十多篇论文、资料等。不少资料是首次面世。如杭州古代阿拉伯文波斯文碑汉译文、乾隆《重修真教寺碑记》、光绪《重修真教寺碑记》、万历《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嘉兴回回“三金四郭”等等。我有了点收获,林老即表扬鼓励。如他1990年7月16日书信中说:“发现云南出版之《回族史论集》,已拜读大作《浙南“复回”刍议》,很好。祝您继续奉献丰硕成果。”拙文《当代“蕃坊”的崛起》发表后,他手机短信云:“色兰!《回族研究》拜读大作,很亲切。”2006年9月银川第二次回族学国际研讨会我们又见面,林老搂抱着我的肩,亲切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看到你的文章,我和老伴就说:‘成美又发表文章了。’很高兴。”我“嘿嘿”傻笑,大师的这两句话真让我陶醉了。
1995年,河南太康马头的朋友开办真空包装牛肉厂,我约请族教名人书写“新月”。中国伊协会长安士伟大阿訇写来了。林老也写来了,还绘制了商标图案。汉字“新月”写3个。商标图案是圆形,底部是弯弯月牙,中间系汉文“新月”2字,上下为阿拉伯文“新月”、“穆斯林食品”。林老有一段关于自己书法的议论,颇有意思。现录后:“嘱我题字,理当效劳。因为乍看起来,不过是一举手之劳,可一挥而就,不象撰稿拟文那样费事。只惜我平生最大遗憾之一就是没练过书法,字迹之拙劣‘有口皆碑’。生人客气不便直说,熟识老友早已赐以美名,曰:‘热爱和平体’,指的是解放初期招贴画。一小孩抱着鸽子,宣传世界和平。其题字‘热爱和平’,取自学龄前儿童手迹。友人本想封我是字为‘娃娃体’,又觉得年龄不相称,且欠雅,故改赞词为‘热爱和平’体。偶或居然能有被邀题字之荣幸,常为此自感受宠若惊。”时代在发展。我和林老的联系方式已从原来的邮寄书信变成了手机短信,以后难见他如此家常式的生动叙述了。那家真空包装牛肉厂因经营不善早垮了,林松教授和安士伟大阿訇的墨宝却留了下来。
我和林老结交二十多年,除去遗忘的,能纪录下来的就是这些在别人看来或许是细碎的小事,但它们对我却是挥之不去,久久不能忘怀的。(作者:郭成美)
小资料:
林松教授(1930- )云南沙甸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作等身,其中《韵译古兰经》,名声赫赫,是现今我国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学术界的顶级人物。(原载《宁夏穆斯林》2008年第1期)
热门关键词: 林松教授
上一篇:缅怀:回族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
下一篇:林松教授的几首赠诗
相关新闻
- • ·缅怀:回族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2015-02-14)
- • ·林松教授的几首赠诗(2015-02-14)
- • ·马强:悼念林松先生,激励来者(2015-0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