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占领的语言:为什么巴以之间不是冲突

▍“我们不是恐怖分子。面对从一登陆我们土地就开始将我们妖魔化成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只是反抗者。” [Getty Images]
社会政治语言的建构从来都不是为反映现实而存在的词语的集合。更多的时候,它是思考之基,以一种促进或妨碍我们特定观念的方式组合。
在定居者的殖民大计中,选词是极其刻意的,意在为种族清洗和定居行为建立一种符合道德的语境。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话语已历经多次变迁。起先,这片被征服的土地被描述为属于这些辛勤的弱者的“杳无人迹的边远之地”。以色列用尽浪漫的辞藻,譬如,“让沙漠绽放”。
由外国移民近来所创立的以色列,例外地获得了西方的深情对待——因为以色列是在欧洲对全体犹太民众进行种族灭绝之后创立起来的。
“给无地之人一片无人之地”的故事是欧洲历史这个骇人章节的完美结局。这是他们的大团圆结局——他们的罪恶感得以缓解。
这是西方唯一想听的、或是只愿意听的故事。
但这是个谎言。
巴勒斯坦有古老的历史,这份历史也孕育出其广博的社会,它的特点在数千年的居住、征服、朝圣、宗教出现、宗教皈依、定居、战争、十字军和自然移民的记载中自然成型。
它的人民中有农民和专家、学者和技师、读者和文盲、城里人和农民。
其社会多元化,不同信仰、民族和种族背景的人们相对和谐地共同生活着。
很多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曾是来来往往的征服者们的战争目标。在他们与当地人融合的过程中,他们留下的印记构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基因、文化甚至是语言的一部分。
一个专有而排外的犹太国家得以建立,唯一方法就是从实际上强制移除这社会,这始于1947年训练有素、资金充沛的欧洲犹太武装团体。

▍叙利亚,1967年。大马士革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Hulton/Getty Images】
当新兴的阿拉伯国家为了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介入时,他们组织不力,部队弱小,装备过时,与当时新建立的犹太国家没有可比性。
根据“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公理,那场战争被描述为以色列的“独立战争”。这可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群外国人入侵并征服了一片土地,夺取了它的城市和花园,然后宣称“独立”于那片土地的原住民。
然后就有了不断支持和宣传其权力的歪曲的语言。
为地方和人重新命名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重塑话语异常热衷,这包括为每一个巴勒斯坦村子和土地重新命名。”
驱逐之后,正如Julie Peteet教授在“巴以冲突中的命名”里所说的,殖民定居者的叙述轨迹一贯否认原住民的存在。
对于以色列人,这种否认相当强烈。甚至在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引发西方反省后,他们的否认仍在继续。最著名的是果尔达·梅厄(前以色列总理)说的,“没有巴勒斯坦人这种东西,他们不存在”。
讽刺的是,1969年,生于俄罗斯的梅厄是在哈伦·拉希德庄园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时说了这句话,而这座庄园是从巴勒斯坦人乔治·贝沙拉特一家偷走的。
大规模破坏或窃取巴勒斯坦遗产的行动随机而有计划地展开。
正如苏阿德·艾米里(Suad Amiry)在《果尔达睡于此》中揭示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到访前,梅厄对雕刻在二层阿拉伯文饰带进行喷砂,来掩盖她生活在一个阿拉伯人家里的事实。

▍很多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曾是来来往往的征服者们的战争目标 [Getty Images]
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重塑话语异常热衷,这包括为每一个巴勒斯坦村子和土地重新命名。
俄罗斯人果达·马波维奇、阿里埃尔·斯柴纳曼、摩西·斯莫兰斯基成了果达·梅厄、阿里埃尔·沙龙、摩西·亚龙。波兰的戴维·古鲁恩成了戴维·本-古里安。白俄罗斯的内森·米雷科斯基成了内森·内塔尼亚胡——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祖父。
为了获得合法归属此地的语境,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更改人名和地名的行为刻意到癫狂,甚至成立了命名委员会监督这一混淆种族和民族身份的、改写历史的巨大工程。
语法的欺骗
“没有任何一种武器可以把一整个国家,连同它的书籍、住宅、村庄、语言、宗教、食物、舞蹈和风俗一起完全抹杀掉”
于是,数千年来根植于欧洲历史、思维、艺术和文化,并在欧洲留有文化遗产的犹太人,为了在已经属于另一个民族的土地上殖民而捏造了圣经部分的故事。
这是一个超乎理解的故事——一群流亡者,在时空、历史和生活都错位了三千多年之后,最终“回归”到了一个遥远的故土。但他们与这片土地没有任何可以眼见的部族、文化、基因或合法联系。
然后不知怎么回事,这个版本的故事掩盖了巴勒斯坦人的版本,哪怕巴勒斯坦的事实建造者,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居住和繁衍了数个世纪。
要将这些摇摆不定、相互出入的虚假叙述嵌入记载完善的历史时间线当中,需要精确而冷酷的欺骗性语法。这只有语言可以办到。

▍加沙,1967年。以色列士兵对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进行审讯。
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把一整个国家,连同它的书籍、住宅、村庄、语言、宗教、食物、舞蹈和风俗一起完全抹杀掉。仅是设想这个过程就已令人心惊。
教授Julie Peteet在她的关于重命名巴勒斯坦的著作中这样写道:“伪造当代犹太社会与巴勒斯坦土地之间的联系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项宏大工程——它关乎语言,关乎地点及其联系,也关于自我及他们的身份认知。”
关于冲突与谎言
“力量悬殊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之间的关系,绝不能够以‘冲突’来概括”
学者们早就指出,在殖民者的语境里,一旦一块处女地落于其手,在当地人做出反应之前,他们的形象就会被勾勒为落后、野蛮、不理性和无故使用暴力。虽然面对攫取土地和资源的入侵者,原住民最终还是会变得暴力。
但这是因为恃强凌弱的话语体系对巴勒斯坦人的否认让他们只能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于是,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恐怖分子”的言论也连篇累牍地出现了。
这种印象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这次起义很大程度上是非暴力的。关于巴勒斯坦男孩用手中的石块与坦克对峙的许多影像,让以色列宣称的“巴勒斯坦人的恐怖威胁论”变得不再令人信服。
然后就有了“谈判”这个话语体系。在这个新的话语体系中,或许最危险、最具误导性的词汇就是“冲突”。
冲突,意为力量相当而平等的双方互不认可的状态。
比如,20世纪40年代德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冲突,同样的,几乎笼罩了整个80年代的美苏冷战也是冲突。但是,力量悬殊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之间的关系,绝不能够以“冲突”来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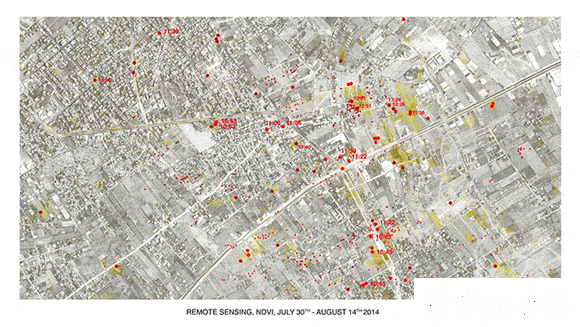
以色列是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他们有迄今已知的最先进的武器,他们在美国乃至全球都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而巴勒斯坦人没有陆军,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他们贫困,他们的自然资源和仅有的生计都面临被剥夺的危险。
他们没有政治力量,没有影响力。他们被包围,被控制,被镇压,被流放,被监押。在一个直白地蔑视和否认巴勒斯坦存在权利的种族主义国家面前,巴勒斯坦人没有任何自卫的能力。
因此,如果要将犹太复国运动描述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那么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雅利安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纳粹主义行径、以及吉姆·克劳法对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隔离,都可以被描述为“冲突”。
频繁使用“冲突”这个词来描述犹太复国运动是一个危险的骗局,并滋生了许多带有误导甚至欺骗性的表达方式:“邻里”被用于描述非法殖民关系;“争端”被用于描述以色列军队在巴勒斯坦村庄里袭击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自卫”被用于指代对无辜生命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轰炸;“安全防护栏”被用于指代隔离被窃取土地的墙;“公民”被用于指代进行准军事占领的非法定居者。
西方媒体口中的巴以“冲突”实际上是:对一整个群体的抹灭;对其历史的删除;对其独特、有名有姓的地理和社会文化空间的切除,即使这些文明从上古时代就已留存下来。
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是美国的吉姆克劳法。这是以色列得以巩固的根基。
而我们不应该继续容忍这些被“冲突”二字草草概括。
最初的欧洲移民们并没有发起一场以“独立”为名的战争。
那些被隔离、专属于犹太人的非法殖民定居点,不是我们的邻居。它们建在被窃取的巴勒斯坦土地上。
我们不是恐怖分子。面对从一登陆我们土地就开始将我们妖魔化成“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只是反抗者——反抗被抹灭的命运,反抗不断涌入我们土地的入侵者,反抗那些自认为上帝赋予其天然可以占有另一个国家的权利的人。
要强行去除殖民的话语体系并破除错误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怕这些观念多么荒唐而没有逻辑。正如Steven Salaita所说:“不要忘了,在殖民社会中,彬彬有礼的撒谎者永远比难以驯服的反抗者拥有更强大的话语权。”
但继续允许或传播这种蔑视社会正义抗争的话语不应该成为一种选择。当我们审视这一切时,对殖民词语的检视、以及对原住民抗争声音的用心倾听,不应缺席。
上一篇:不是伊斯兰孕育恐怖主义,而是恐怖主义抱伊斯兰大腿
下一篇:伊斯兰传统中的和平观(上)
相关新闻
- • ·对话之礼仪(2009-12-20)
- • ·真诚地展示自己 - 礼仪社交(2009-12-22)
- •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礼仪(2009-12-22)
- • ·人际交往要适度不要过度投资(2009-12-22)
- • ·现代社交礼仪特点(2009-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