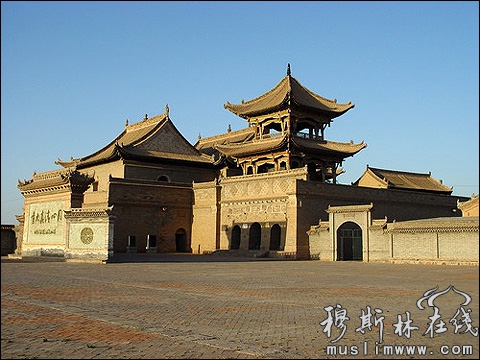
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韩星
韩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
摘要:论文以回族为例,考察、分析伊斯兰教进入中国1300多年发展的历史,总结伊斯兰教与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交流、融会,成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的历史经验,并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可以为中国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伟大复兴和走向现代化,为当代世界文明多元共存,和平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伊斯兰教;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会
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开始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和演变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唐、宋、元三个朝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时期,迄止明代,中国先后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各穆斯林民族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习俗产生了深刻影响。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合,成为各穆斯林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出于对宗教的禁锢和否定态度,在谈到少数民族时,往往只谈民族文化而不谈宗教文化,或者简单地把二者对立起来,这样就导致对信教少数民族历史的片面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十分注意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融会,这里的“西”主要是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这本身就是不全面的,而“中”则主要是儒家文化及其辅助道、佛等,似乎中国文化就是汉文化,海外学者更是把中国文化与汉文化相提并论,忽视了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的,除了儒、道、释等文化传统以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亚文化系统,象回族这样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实际上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应忽视这些亚文化体系。
一、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交流、融会的前提和基础
1、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化体系,二者多有相通之处。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化体系,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①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各自又都是博大精深的综合性的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本身就是阿拉伯帝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它兼收并蓄,广泛继承了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的成就,将东西文化熔化为一炉。“它不仅是古代各种文化的拼凑,而是原有文明的新的综合。它虽然来源不一,但却明显带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特征。”②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以后,伊斯兰哲学与中国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观念相互融通,铸造出以回族为主的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教是一种入世性很强的宗教,即兼具宗教性和世俗性,或者说宗教性和世俗性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纯粹宗教的意义上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佛教等全体宗教一样,是一种精神信仰。但实际上对一个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远远不止这些,它还是一种价值观念,一套完整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一种文化体系以及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将神圣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信仰与实践一体化的生活方式”。与佛教、道教等宗教不同,伊斯兰教并不远离人间烟火,清真寺常常不在深山老林,而是居于社会中心,与教徒的世俗生活密切结合。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宗教象伊斯兰教那样,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也没有那一种宗教象伊斯兰教那样世俗化。你很难分清伊斯兰教中什么是宗教性的,什么是世俗性的东西。这一特点与伊斯兰教的“两世幸福观”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作为一种宗教,往往把一种虚幻的、彼岸的、天国的幸福作为真正的幸福,要人们通过信仰和修行达到彼岸和来世去获得这种幸福。如佛教、基督教认为今世为痛苦、为灾难、罪恶,通过对现实的否定引导人们追求来世的幸福,而伊斯兰教则不同,它不以否定现世的幸福为前提来追求来世的幸福,而是既重现实生活的“今世”,又重复活后的“后世”,鼓励穆斯林为获得两世幸福而奋斗。《古兰经》说:“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后世的报酬。”(31:45)甚至穆罕默德本人也向真主祈求两世幸福。这些特点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非常相近,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但本质上是宗法伦理型的世俗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的、注重现实生活的学说体系。中国传统的道教是一种宗教,其基本思想倾向对现实、人生的虚无主义观点和对出世主义的逍遥境界的追求,但由于有儒家的强烈制约,它对现实的否定是有限的,它的出世是成神成仙,是在现实的条件下对人生的超越实践,其实儒家也有超越精神,只不过不是成神成仙,而是成贤成圣。儒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是一种互补结构。佛教进入中国以后,经过了漫长的传衍,最后也中国化了,在仍然追求彼岸世界是同时,不得不接受儒家某些思想影响,承认现实皇权以及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其基本重心也从重成佛进天国转移到普渡众生,劝人为善方面来。不过,相比较而言,伊斯兰教两世幸福基点是后世是幸福,对后世生活的憧憬,往往成为一般穆斯林整个现世生活的最终归宿,这与中国文化以现世生活为基点,在肯定对人生、社会的前提下,对人生境界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不同,反映了伊斯兰教是以宗教为本质的,中国文化是以哲学为核心的。
伊斯兰教与世界上其它宗教比较起来,其最大特点是非常强烈的政治性,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种政治性的宗教。自伊斯兰教创立开始,宗教与政治之间就几乎没有什么界限,宗教社团就是国家,宗教领袖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宗教的传播发展就是疆域的扩大延伸,宗教的经典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法律。伊斯兰教教义认为,世间一切权力都属于真主以及服从真主,服从真主使者穆罕默德,以及服从穆斯林中的具有权威的人。这样,整个政治体系都是建立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之上的。伊斯兰教理想的国家模式就是“政教合一”。这点与中国文化也非常相似。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政治性。古代中国也有“政教不分”。不过,这里的“教”不是“宗教”的“教”,而是“教化”的“教”。上古政治倾向于社会性的教化,三代之“教”倾向于学习参政、议政。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起争鸣,提出了各种学说,但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求治”。周秦诸子的政治精神,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求治”为目标的思想范式奠定了基础,在其后两千年的历史上形成了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教育等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
伊斯兰文化中也有类似于中国“中庸之道”的思想,例如,在钱财问题上,伊斯兰教既反对吝啬,也反对过分,其倡导的消费原则是正当、道德、适中,《古兰经》要求穆斯林“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25:67);在对待日常的物质生活方面,《古兰经》主张人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7:31),就是说既不要禁欲,也不要纵欲;对待敌对的进攻,《古兰经》主张“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不喜爱过分者”(12:190);在礼拜颂经时,《古兰经》要求“不要高声朗诵,也不要低声默读”,而“应当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17:10);对待前定,伊斯兰教既承认前定,又反对宿命论。在伊斯兰教派中有“麦吉尔教派”,又称“中庸派”,其主要纲领是不卷入各种纷争和内乱,把一切交给真主判断。①
伊斯兰教追求知识,崇尚理性,这与中国文化也相当接近。《古兰经》说:“真主的仆人中,惟有学者敬畏他”(35:28),“真主以真理造化这一切,他向有知识的人解释种种迹象”(10:5),“你说:‘有知识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穆罕默德的圣训说:“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天职”,这就把学习任务提到最高的限度。又说: “你们要学习,从摇篮学到坟墓。”这就说学习必须持之以恒,即活到老学到老。还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信士死亡后的永垂不朽的善功,便是传授知识,阐扬文化,留下优秀的子孙和益人的著作……”。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科学昌明,学术活跃,追求学问蔚然成风,无不与《古兰经》崇尚理性,倡导知识有关。中国文化崇尚实用理性,尊崇知识,爱好学习,是人所共知的优良传统。
伊斯兰教非常注意人的道德修养,《古兰经》云:“凡敬畏而且修身者,将来都没有恐惧,也不忧愁”(7:35),“凡培养自己的性灵者,必定成功……”(91:9),“洗涤身心者,……真主是惟一的归宿……”(35:18),“有教养的人确已成功……”(87:14)。穆罕默德的圣训说:“我的使命就是为了完善人类的道德。”“你们中最优秀者,乃是你们中道德最高尚者。”这些说明,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核心,是重在培养人的优良道德品质。对一个穆斯林来说,良好的道德修养是其成功人生的重要前提。从《古兰经》中可以看出,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还有关乎个人修养的“德之容、德之音、德之举”以及大到治国、治世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不过,与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理论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倡导的道德修养,无不与对真主的“敬畏”和“归顺”相提并论,无不与穆斯林能否获得两世吉庆紧紧相连,使其赋予了一种至尊、至贵、令人神往的精神力量。这是伊斯兰教有别于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地方。
2、伊斯兰教的经济基础是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贸经济,与中国农耕经济模式不同,但可以互补。
伊斯兰教是产生于世界沙漠最多的地带,最初由一个游牧部落发迹,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这是它大陆游牧精神宗教化的成功。所以伊斯兰教的宗教行为,是带有浓厚的大陆游牧文化的色彩,有它的坚决性、彻底性、冒险性、流动性,其特长是经商。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形态,稳定安居是农耕经济发展的前提。这样就形成了其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爱好和平,兼容并包的特点,对于游牧民族中国人历来都是鄙夷和防卫和双重心态。文化把他们当成狄夷,在军事上又不得不“修障塞、饬烽燧,屯戌以备之。”①但是,当有游牧民族进入中国的文化之中以后,中国文化往往发挥其强大的融合能力,慢慢地将其消化。
阿拉伯游牧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贸经济,在进入中国农耕经济中以后,一方面有一部分穆斯林后来从事农业,与中国经济完全重合,另一方面,继续从事商贸的穆斯林也逐渐适应了中国以农业为主体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成为中国经济的有力补充。这成为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流、融合的基础。
上一篇:从“希吉拉事件”到“乌玛”政权——穆罕默德传创伊斯兰教的历史
下一篇:圣城之血:第二次耶路撒冷大搏杀
- • ·谁代表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2011-10-10)
- •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2011-08-16)
- • ·《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2011-12-19)
- • ·《伊斯兰常识问答丛书》总序(2012-01-26)
- • ·别再说回教,应称伊斯兰教(2009-12-21)







